周济院士的学术人生,宛如一场在材料科学世界的寻路之旅。他以超材料为墨,以微观结构为纸,在常规与超常的边界挥毫泼墨,绘就功能材料的崭新图景。他不仅是实验室里的探索者,更是材料王国的建筑师。他三十余载躬耕不辍,将思想的种子播撒在学术沃土,终使中国功能材料研究如兀立的山峦,在国际科学版图上显露峥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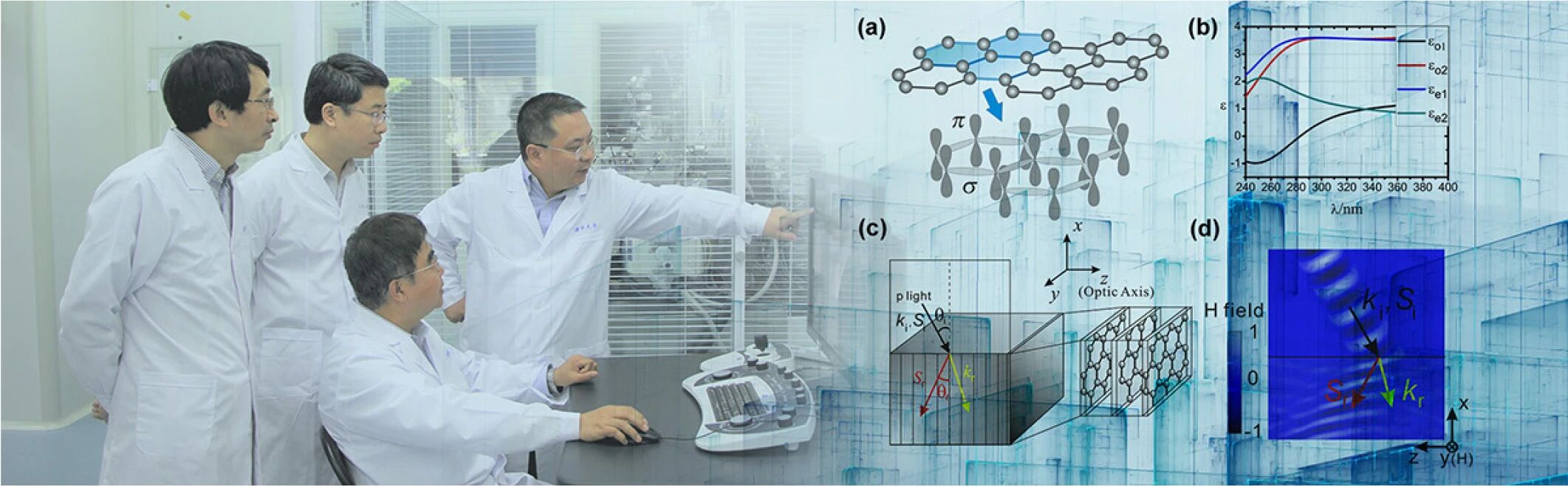
周济院士团队(图片来源:清华新闻网)
从电子元件到超材料:清华团队的成果与进展
周济1991年从北大博士毕业来到清华工作,在李龙土院士的引领下进入了国家当时最亟需领域,攻坚无源电子元件的片上化问题。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等三大类无源电子元件需要利用多层陶瓷技术将电磁介质与金属导体共烧,其核心难题是获得具有良好的物理特性和工艺特性的陶瓷介质。其中,电感器由于结构相对复杂,片化步伐较慢,成为无源电子元件发展的瓶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才出现基于多层陶瓷技术的片式电感器。我国虽然从国外引进了相应的器件生产线,但材料却受到禁售和专利垄断的双重封锁。在这一形势下,周济投入到片式电感器材料研究中,利用纳米烧结动力学原理成功开发出兼有高性能和低温烧结特性的软磁铁氧体材料,既打破了封锁,也成功绕开了国外专利,为此后我国片式电感器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优势。
解决了电感器生产的难题后,周济很快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作为有源器件的各类半导体器件早已实现了大规模集成化,而以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为代表的、相对简单的无源电子元器件却长期以分立的形式用到电路当中。能否借助于多层陶瓷技术把各类无源元件整合起来?低温共烧陶瓷技术(LTCC)的出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沿着这一思路,周济院士团队从材料的理性设计出发,提出了一种介电常数可以大幅度调整的低温共烧陶瓷基体材料,使无源电子元器件的集成成为可能。
近20年来,周济投身于超材料研究,发展出非金属基超常电磁介质等世界领先的新材料。超材料是世纪之交出现的新概念,通过人工设计的功能单元实现自然材料所没有的性质。早期开展超材料研究的科学家主要是物理学家和电子科学家,主要关注新奇的性质;周济团队则是国际上最早从材料领域进入超材料领域的团队。与当时其他研究者的视角不同,周济发现超材料不仅代表了一大类具有特殊性质的新材料,更是一种材料构造的新方法或新研究范式,这样的新方法或新范式有望把材料研发从“炒菜式”模式中走出。
从电子学学士到材料大师:院士走过的跨学科之路
周济直言道:“就我个人而言,跨学科背景对我做科研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这种重要性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多学科的教育背景构成了一种知识结构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对每个科学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科学研究本身是创造性工作,只有他人没做或者做不了的工作才有意义,因此每个科研工作者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而打造这种独特性的一个捷径就是跨学科的学习。第二点体现在科研选题上,有了跨学科的知识积累更适合探索学科交叉的问题,对科技前沿的视野可以开阔一些,选择科学问题的范围也就更大,更容易找到好的、更适合自己去做的题目,而交叉领域往往是一些容易产生新成果的领域。第三点体现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有了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更有益于打破常规,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我们在材料领域取得的一些科研成果就得益于来自物理学、化学、电子学等领域的借鉴。”

2022年6月,清华大学第一届折纸超材料大赛,前排右1为周济
“读研究生是跨学科的一次机遇,”周济说,“我积极鼓励大家在选择读硕士生、博士生或者做博士后时能走出舒适圈,勇于领略不同学科的风景。”至于判断哪些新学科适合自己,周济认为应该考量两个方面:一是兴趣,对做科研的人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就有了探索是动力和激情,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二是要发掘自己的强项,知道自己适合做哪一类研究,在此基础上培养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独立思想与创新意识:青年学子的必要品质
周济认为,做科研要有独立思想、敢于打破常规、面向国家亟需领域做“探矿者”。与应试教育体系不同,科研最重要的是独立思想、科学精神与创新意识。如果依然秉持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思维,大家的想法、思路、选择都高度一致,缺乏个性,就会带来内卷。“现在各行各业都内卷,产业界内卷,学术界也内卷,”周济说,“而科技界和学术界内卷的应对方案很简单,就是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尽可能不去走别人的路。”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陈寅恪教授曾提到讲课有三不讲原则:书本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周济将陈先生的“三不”原则用到自己的科研中,要求学生和助手们“文献上有的工作不做,别人正在做的不做,我们自己做过的也不做。”因此,周济团队做科研从不跟风,从不追热点,既有效避免了在科研圈的内卷,也保证了科研的开拓性和特色。
周济还提到了清华百年校庆时的电影——《无问西东》,影片中几代清华人的人生抉择都是来自于独立思考,而非随波逐流。在影片中,吴岭澜读书时迷失在“理工科才叫实业”的理念中,他努力学习却疑惑不解、自我怀疑,找到梅贻琦校长谈心。梅校长鼓励他:人把自己置身于忙碌之中,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却丧失了真实。“这句话实际上来源于梅校长的一次演讲。所以我想跟大家讲,未来的中国,需要一批能独立思考、引领世界科技前沿的探路者,这正是我们清华人的使命。”
对话周济
提问:您当年因为一些器件新材料被禁售和垄断而转投到材料研究,最近20年又投身于超材料研究,请您谈谈材料科学发展对社会的意义。
周济:材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世界是物质的,而有用的物质就是材料。在当代科技发展进程中,材料往往扮演着基础和先导的作用。首先说基础作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医学等的发展水平都依赖于材料的水平。通过分析“卡脖子问题”,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问题来自于材料。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讲,没有好的材料技术基础,很难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再说先导作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变化的驱动力正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即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我们追溯信息革命的技术源头,一定会追溯到上世纪中叶半导体的发现,正是由于这一材料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才导致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支撑了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超材料既属于材料家族的一个新分支,也与传统意义上的材料有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如果说,对物质的建构产生了材料技术,对物质的解构产生了材料科学,那么对物质的重构产生的就是超材料。超材料试图通过人工设计功能单元来获得自然材料不具备的新性质,因此有望在很多领域产生变革性的技术。比如用超材料可以做成没有像差的透镜、高速低功耗的计算机、同时具有低密度和高强度的建筑材料等。总之,当材料的性能达到自然极限后,我们可以利用超材料打破这些极限,因此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提问:材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起到什么作用?
周济: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行时,一系列的新科技将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材料在这些新科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我们都看到了AI对未来的深远影响,而AI的基础是算力,尽管当前AI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算力瓶颈已经凸显。目前各国用于训练大模型的能耗已占到了全球能耗的2%左右,按照AI应用的速度,每年都会成倍增长,以至于全球的发电量全都用在AI上都不够用。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关键可能还是材料。最近的研究和论证表明,利用超材料强大的光调控功能实现高效、低能耗的光计算,很可能成为解决未来AI算力及其能耗难题的路径。另外一个例子是具身智能技术,它将人工智能应用逐渐从虚拟环境拓展到物理世界,如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无人机应用等。这一技术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影响更大。而具身智能技术重要的基础依然是材料,是大量的具有不同功能的材料,如传感材料、计算材料、智能材料、仿生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等。没有这些材料的支撑,具身智能是无法发展的。